科玄论战”之当代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4日
作者:记者 张清俐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过去90年,但论战涉及的问题至今仍未彻底澄清。而较之“科玄论战”所发生的20世纪初,在科学技术迅疾发展的21世纪,今日对科学与人文价值的认识在新的时代问题域中更具现实意义。本期“学海观潮”邀请洪晓楠、何中华、曾昭式、李醒民四位学者围绕“科玄论战”各抒己见。
对话人
洪晓楠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何中华 山东大学教授
曾昭式 中山大学教授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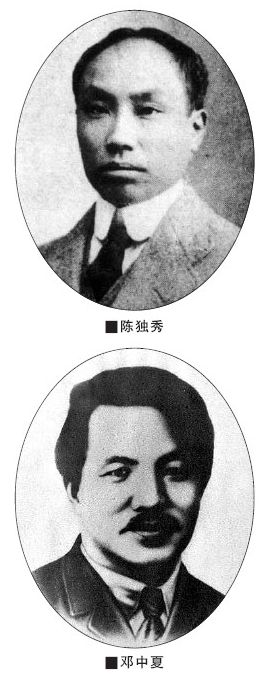
洪晓楠:20世纪“科玄论战”的讨论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如何看待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人类创造的文明史来看,科学与人文有着一致的根本目的,即都是为了洞悉世界,以便改造世界,推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睁眼看世界,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中,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路。进入21世纪的当代中国,一方面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
缘于有关中国道路的观念冲突
此次论战是中国现代时期的重要事件,说是重要事件,在于不能把它简单归于思想、文化、学术、科学或哲学某个领域的讨论,因为它涉及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变革,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学人探索中国出路不同观念中的一次冲突。
李醒民:1923年在中国科学界、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爆发的“科玄论战”(又称之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有其发生的深刻时代背景。从国际情况看,一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经典科学的危机引发的“科学破产”的悲观情绪,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对欧洲物质文明乃至其发达源头科学的怀疑和绝望。从国内情况看,它是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碰撞或冲突的继续,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积极引进西方德、赛二先生的科学派或革新派与文化保守派或国粹派的思想较量。玄学派反科学既是对当时国外反科学思潮的呼应(丁文江、胡适等都揭示了这一背景),亦是西方科学和技术进入国门以来封建士大夫阶层本能的排异反应和自觉的抗拒行为的继续和延伸。
洪晓楠: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科玄论战”的爆发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论战发生于后五四时期,可以说,“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为论战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背景,而中国走向近代(或现代)的过程,则构成了其更加广泛的历史前提。具体来说,“西学东渐”造成的东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遭遇和汇合是“科玄论战”发生的远因,后五四时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巩固以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是其近因。
曾昭式:此次论战是中国现代时期的重要事件,说是重要事件,在于不能把它简单归于思想、文化、学术、科学或哲学某个领域的讨论,因为它涉及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学人探索中国出路不同观念中的一次冲突,类似这样的论战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东西文化之争、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论战,以及中国社会性质之争等。从学术、文化、科学、哲学、意识形态等领域寻求中国未来之路。
何中华:从某种意义上说,“科玄论战”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相遇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一场观念冲突。东西方文化的相遇及冲突,隐藏着多层面的含义。比如说,在文化的时代性维度上,它表征为新学和旧学的矛盾;在文化的民族性维度上,它表征着西学和中学的矛盾;在文化的内核意义上,它又意味着理性与价值的纠结。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不积淀在当时中国的每一位关注中国命运和中国文化前途的学人心中,以至于构成一种难以打开的情结。风云际会,这一系列的不相侔,都缘自“科玄论战”这一看似偶然的文化事件而以格外显豁的方式集中迸发出来。当时直接参与论战的文字,就达几十万字之多,为学术界所少见。参与的学者,不仅涉及的专业面相当广泛,而且人数众多。
加剧三个文化哲学阵营的分化
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的哲学舞台上,逐渐形成了中国现当代的保守主义派文化哲学、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可以说,这三派文化哲学思潮形成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大三角”。“科玄论战”将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三派文化哲学阵营的营垒分化得更加明确。
曾昭式:参与“科玄论战”者大致分科学派(如丁文江、胡适、王星拱、吴稚晖、任叔永、唐钺等)、玄学派(如张君劢、林宰平、梁启超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三个阵营,讨论的问题可粗略概括为三个方面:科学问题、科学与人生观和科学的社会功能。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讨论。
洪晓楠:“科玄论战”涉及的问题虽然十分广泛,但争论的焦点可以归结为科学究竟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如果深究下去,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真正的焦点则在于:传统(玄学派)与现代(科学派、马克思主义派)的对峙、科学(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人文(人文知识、人文精神、人文方法)之间的对峙。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对当时国家、社会的迫切需求和未来道路选择的认识和判断是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他们“以现代化批判传统”;玄学派实际上是一批主张批判西方现代化的学者,或者说是对西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学者,他们希望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以纠偏西方现代化之弊,“以传统批判现代化”。随着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深入以及科学派和玄学派在科学与玄学关系问题上论争的展开,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相继参加论争,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玄学派与科学派的观点进行批评,从而形成了论战的第三方——唯物史观派。尽管陈独秀、瞿秋白在“科玄论战”中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出现,在科玄两派之间,他们显然更同情并接近科学派的立场和观点。
何中华:“科玄论战”基本格局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间的博弈和交融。但总的说,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科学派学者是“同路人”。陈独秀、瞿秋白都对科学派的观点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质性传播,是在五四运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而五四运动的口号是德、赛两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也就是说,启蒙精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文化语境。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启蒙的意义上被诠释了。这也是“科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何以同科学派更加接近的一个重要原因。玄学派代表传统的文化精神,而马克思主义是以反传统的姿态进入中国的,所以不可能同玄学派达成一致。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始终是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和使命。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走怎样的路才恰当?不同立场、不同学术背景、不同价值取向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答案。玄学派思想家主要是基于文化的民族性立场,着眼于捍卫中国文化的道统,在面临西方文化同化的压力下,试图从精神价值层面拯救中国文化的命脉。这种文化焦虑,开启了现代新儒家的先河。科学派学者则主要着眼于文化的时代性立场,认为只有西学才代表中国的未来,其中隐藏着一个“全盘西化”的假定。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于从科学视野去阐释马克思主义,试图从经济变动和历史进化的角度为中国革命寻求合法性。就此而言,“科玄论战”的确折射出各个不同的学派或思潮的独特文化诉求。
洪晓楠: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的哲学舞台上,逐渐形成了中国现当代的保守主义派文化哲学(以现当代新儒家为其主流)、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可以说,这三派文化哲学思潮形成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大三角”。实际上,可以说,“科玄论战”是东西文化论战的继续:“玄学派”是东方文化派;“科学派”是西方文化派,也是自由主义派、实证主义派。“科玄论战”将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三派文化哲学阵营的营垒分化得更加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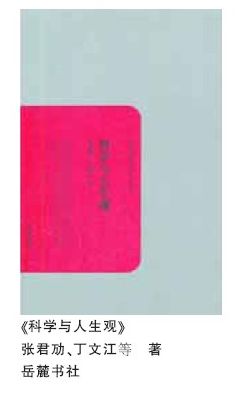
推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与发展
此次论战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推动了中国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启蒙与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的确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
李醒民:我认为,将“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的倡导者贬斥为“科学主义”,这是对历史的误读。中性的科学主义的含义是,科学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典型看法和观点。但是,人们经常在赋予科学以超越于其合理范围和限度的绝对权威这一贬义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它。玄学派之所以站在反科学的立场上,主要还是对科学的精神价值的文化底蕴缺乏了解。在他们眼中,科学不过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器而已——张君劢曰:“电灯、电话、自来水”“科学也”——难怪他们把科学等同于船坚炮利、务外逐物、赚钱求利,甚至认为科学损美败德。他们不仅认识不到科学的形而上意义,反而把科学派探究科学深层底蕴的深邃洞见和发挥科学文化功能的良苦用心斥为科学万能论或科学主义。
洪晓楠:“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张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后来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的发展。一方面,他们的科学方法泛化的主张,使得他们在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问题时,夸大了文化的时代性,从而导致全盘西化的立场。从胡适的全盘西化到第二代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殷海光的西化论,即是明证。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辈的科学主义立场受到后继的自由主义新生代的批评。林毓生即提到胡适过分渲染的“科学主义”是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从而导致流行的科学主义未能提供对科学的本质及其方法更切实的领悟与理解所需的资源。林毓生对“科学主义”兴起原因的分析非常深刻,但是,他对“科学主义”后果的分析也遮蔽了科学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的“科学”大旗的维护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盛行、而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科学派反对玄学派贬低科学的方法,提倡“玄学”或“新宋学”,而主张“科学的人生观”,无疑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思想启蒙,这也是科学派在这场论战中能得到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的重要原因。
此次论战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推动了中国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启蒙与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的确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从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岁末,其间唯物史观派对形形色色的唯心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批判,宣传了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科学地解决人生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在唯物史观派看来,科学派则并没有或未能解释“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比如邓中夏在总结三派观点时指出:“科学方法派大概都是学过科学的,他们的态度,第一步是怀疑,第二步是实证(拿证据来);他们的主张,是自然科学的宇宙观,机械的人生观,进化论的历史观,社会化的道德观(皆见胡适之上海大学演讲辞)……唯物史观派,他们亦根据科学,亦应用科学方法,与上一派原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他们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这是他们比上一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的所在。”邓的评述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除此之外,邓中夏还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科玄论战”进行了总结:“东方文化派可以说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称宗法思想),科学方法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劳资两阶级尚有携手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唯物史观派力图表明历史观与人生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的历史观,也奠定了新的人生观。此次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唯物史观逐渐占领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的高地,并成为中国现代思潮和时代发展的引领者。
打破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的对峙
在当下,“科玄论战”之关注问题并未解决,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精神家园的建设亟待解决。面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问题,“科玄论战”给我们留下许多可资反思的经验。
曾昭式:关于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已有不少学者研究,对论战中不同派别主张的审视离不开其发生的时代背景,对历史上思潮云涌的客观公允的回顾与评价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更有益于启发我们对当代问题域的回应与思考。其实,在当下,“科玄论战”之关注问题并未解决,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精神家园的建设亟待解决。面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问题,“科玄论战”给我们留下许多可资反思的经验。
文化选择之目的在于寻求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出路,西化派与中学派两种选择均非正确。就西化派而言,他们是站在西方文化立场审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并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观念是不可取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起来、传递下来的生活方式,因此,对于文化传统,必须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全盘西化”论带来的是文化的混乱,把人们引向崇洋媚外。而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人,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吸收西方文化的“坚船利炮”和科学方法。这种观念更多强调的是文化的继承性、连续性,而忘了文化发展的间断性或创造性。其实这两种观念在学人身上都表现出文化建设的无所适从,且不说他们面对纷至沓来的不同文化需要消化,对于如何寻求适宜于中国发展的新文化,他们也进行着痛苦的思索。
李醒民:“科玄论战”是20世纪初革新派与保守派思想较量的继续和发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场论战中涉及的诸多问题,在当时既有学术和理论价值,也有现实和实践意义。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后现代派和国粹派合力搭班,还在上演类似的戏剧: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结成“神圣同盟”,打出反科学主义的旗帜,把人们正在设法医治的现代社会病统统归罪于科学。反科学或反科学主义在理论上是空中楼阁,在实践中是因噎废食,根本站不住脚。可以预料,他们的结局不会比当年的玄学派好到哪里去。
何中华:恰当的态度应该是寻求科学与人文的互补和均衡。从人的存在的角度看,无论是科学文化还是人文文化都是必要的。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是人作为肉体存在的自我肯定方式,而人文则是人作为心灵存在的自我肯定方式。就个体的人而言,在人格成就方面,一个人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必须要养成健全的人格。科学与人文就像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当然,必须承认,科学和人文作为两种文化、两种精神,是存在着矛盾的。这种矛盾不是虚构的,也不是假问题。它深深地植根于人的存在的二重化,即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的分裂。但是,从应然的角度说,科学与人文的冲突是应该消除的。唯其如此,才能真正优化人的生存方式,使人的存在走向健全。所以,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了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这个人类致力于努力的目标。
洪晓楠:在我看来,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作为彻底的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作为彻底的自然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人本主义”,是一个更为全面的纲领。马克思哲学内蕴着“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本主义”两条线索,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使有关价值论的问题长期处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视野之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随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再认识的逐步深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回到马克思,从而对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重新发现和创造性解释,致力于弥合事实与价值、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两分的鸿沟,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与互动,进一步推进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新发展。

背景链接
“科玄论战”所涉及的人物在当时极具代表性。参加论战的既有著名的哲学家,如梁启超、胡适、张君劢、张东荪、瞿菊农、范寿康等,也有著名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如丁文江、任叔永、王星拱、唐钺等;既有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如梁启超,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如陈独秀、胡适;既有国民党的元老,如吴稚晖,也有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争论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北京的《努力周报》、《时事新报》、《晨报》,上海的《东方杂志》、《学艺杂志》、《中国青年》,广州的《新青年》等拥有广泛读者的知名报刊上,影响巨大。
“科玄论战”的主题虽说是科学与人生观(玄学)的论战,然而在论战的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域相当广泛。据当时参战者之一唐钺在《“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一文中所做的不完全总结,大致有:(1)人生观与科学的异点;(2)人生观与玄学的关系;(3)科学的分类法;(4)论理学(包含概念、推论等)与科学的关系;(5)物和心;(6)知识论;(7)纯粹心理现象与因果律;(8)科学教育与修养;(9)人生观和情感的关系;(10)情感和科学方法的关系;(11)科学与哲学的关系;(12)科学的性质;(13)科学与考据学的关系。
在“科玄论战”中,三派代表人物的主要分歧在于:玄学派代表张君劢主张,第一,力主划清科学与玄学(哲学、人生观)的界限;第二,反对科学万能,而不反对科学;第三,“欲提倡宋学”。与玄学派力主划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不同,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则强调科学与哲学的联系,以科学的泛化与实证论化为前提,强调科学的方法在各个领域都普遍适用。而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力图以唯物史观为思想资源超越科玄两派。在论战中,陈独秀坚决反对张君劢、梁启超的观点,同时也不同意范寿康的先天的形式说和任叔永的“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说法。陈独秀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这次论战中也暴露了对唯物史观作科学主义解释的倾向,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有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倾向等。
来源链接:http://www.cssn.cn/zhx/zx_zxdh/201503/t20150305_1534924.shtml
|